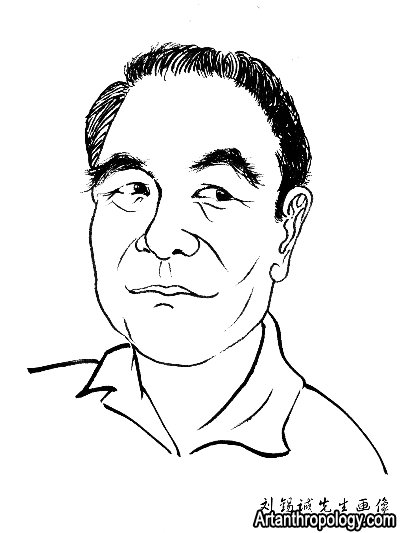
中国文化报2014-07-25
本报记者李静
“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
刘锡诚,男,1935年2月21日出生,山东昌乐人。文学评论家、民间文艺学家、文化学者。1957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民间文化论坛》杂志特邀主编。
今年是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刘锡诚的八十寿辰,来自各方的祝福从年初开始延续至今。3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还联合为其召开“刘锡诚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这一切都证明了各界对其学术水平和人品人缘的充分肯定。
刘锡诚从事学术研究60年来,致力于民间文艺、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学术上,先生锐意开拓,治学严谨,视野宽广;生活中,先生为人宽厚,奖掖后学,堪为学界翘楚。”这是业内人士在“刘锡诚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上对其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原主任祁连休说,刘锡诚的学术经历,贯穿了我国当代民间文学的发展史,其学术道路可以说是我国当代民间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民间文化已融入血液
刘锡诚出生于山东昌乐一个普通农家,“父母一生靠在黄土地里刨食吃过日子,我也学会了一年四季的全套农活”。刘锡诚的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柳体的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父亲对我总是抱有望子成龙的心情,常给我讲一些他所知道的历史故事,比如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我一直记忆很深。”
1953年夏,刘锡诚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土布对襟褂子,到北京大学俄文系报到。“据说之前我们那个几十万人口的县城还没有一个人上过这所大学。”刘锡诚说。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4年时光,刘锡诚不但读了不少俄文小说,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时任俄文系主任、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研究家曹靖华,“先生授课时慢条斯理、抑扬顿挫的河南口音,至今还在我耳际萦绕。”
刘锡诚毕业论文的导师就是曹靖华。他决定以民间文学作为毕业论文,得到了曹先生的赞同,并给他开列了中文、俄文的多种参考文献。毕业前夕,曹靖华又把刘锡诚叫到办公室谈话,表示要介绍刘锡诚到中国文联工作。刘锡诚受宠若惊,当即表示同意,从此踏上了文艺之路。
大学毕业后,刘锡诚曾先后任职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编辑部和文艺报社,也担任过新华社的记者和编辑,“但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已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情。后来在面临很多选择时,我毅然放弃了俄罗斯文学和新闻工作,中断了已小有成绩的文学批评,最终选择了备受冷落的民间文学研究。”
做田野调查很幸福
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既要伏案做很多资料搜集和考证工作,又要深入穷乡僻壤做田野调查。刘锡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到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足迹更遍及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云南、贵州等老少边省区。
1965年9月末,刘锡诚奔赴西藏错那县勒布区一个门巴族聚居地采风。对于那次田野调查,刘锡诚至今记忆犹新。“进山之前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三件事:找一位当地的向导;向老乡借一匹性情温顺点儿的马;到县上仅有的一家供销社买一斤高级糖,一旦没有饭吃,可以用来充饥。”刘锡诚说得很轻松,其实背后的行程十分艰辛。西藏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刚刚还是艳阳高照,转个山口可能就会下起瓢泼大雨。“雨点借着雨势像雨箭一般迎头向我们射来,心情却格外激动。”几经周折,刘锡诚一行终于寻访到了那位脑子里装着很多门巴族民俗知识的老牧民。“那位牧民住在一间孤零零的土房子里,里面很黑,几乎没有什么家当。好客的主人在屋子中间点起了火堆,拿来了糌粑,在明灭的酥油灯下为我们讲述他们民族的故事,一个神秘而有趣的世界。”夜深了,刘锡诚便与主人“仰卧在被篝火烤得温热的地板上,拉过来发出阵阵膻味的老羊皮盖着”,他觉得很幸福。
近年来,刘锡诚依旧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坚持做田野调查。2012年底,刘锡诚借在贵阳参会之便,冒雨前往贵州省清镇市龙窝村造访苗族歌师。“先生是北方人,听贵州清镇的汉族方言本就十分困难,更何况是苗语唱诵,再加上先生年纪大了听力不好,在当地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坚持细细辨听,回去后又多方查找资料,写成了《走马苗寨》一文。而我这样的本土学者,却至今没能将那些唱段完整地摄录下来,实为愧疚。”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余未人说。
像这样艰苦的调查,刘锡诚一辈子经历了很多。1960年,他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农牧民中生活过一年。上世纪80年代,他曾到云南沧源佤族聚居地调查过沧源岩画,到广西三江调查过民间文学,到新疆的尼勒克调查过哈萨克民间文学……但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并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在没有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会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刘锡诚说。
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
翻阅刘锡诚送给记者的一本《刘锡诚文章著作要目》,密密麻麻70页写满了这些年他出版的书籍的书目,从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到近几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林林总总全是先生的心血,其中有两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民间文学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些空白。
一是《中国原始艺术》的出版(199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化、原始思维难解难分的联系。从1992年秋天起,我花费了差不多6年的时间,系统阅读考古发掘的报告和考古学的著作,最终完成了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刘锡诚说,不研究原始艺术及原始先民的逻辑思维方式,就难于知道和破译民间文学的所来之径和所包含的内容之神秘、斑驳和多样。已故民俗学大家钟敬文看到《中国原始艺术》出版后非常欣喜,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过去有关原始艺术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外国原始艺术的,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书,更没有中国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
二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出版(2006年,河南大学出版社)。“从我在北大读书时起,就开始积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的史料,再加上50年代、80年代前后两度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也积累了大量的学科发展史料。进入21世纪,从学科讲,百年的民间文艺学史要求有理性的回顾和总结;从个人讲,到了70岁,也有一种时不我待之感。于是,2003年,我下决心写一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理清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理论体系。”刘锡诚说。这部98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现已成为我国许多高校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生的参考书。“有生之年,我还会做修订,以弥补批评家们指出的不足,使其更尽如人意。”
现在是进行冷静科学反思的时候了
刘锡诚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其实,先生还有另一个重要头衔值得自豪:他是改革开放之后较长一段时期之内(1983—1989),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利慧说,上世纪80年代刘锡诚在主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就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我国民间文艺界的学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这个工程随后的开展同他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他的一些思考、工作方式也给三套集成留下了特殊的烙印。
自2003年非遗保护工作启动以后,刘锡诚又被文化部聘为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十分珍视这一头衔,自觉地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走出书斋,参加评审、辅导、督察工作,并撰写一些文章,积极为各地工作建言献策、答疑解惑。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深有感触地说:“在我们开展相关教育和保护工作时有许多困惑,比如,迷信与俗信应该如何区别?我们该如何看待民间信仰?刘先生于2005年写的一篇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的问题》,充分肯定了民间信仰的价值。他引用顾颉刚《天地间的正气》中的一句话:‘情歌,是从内心发出的。宗教的信仰,也是从内心发出的。这两种东西的出发点和它的力量是相同的,同样是天地间的正气。’这篇文章解答了我的一些困惑。”
刘锡诚虽是80岁老人,但对非遗工作的思考从未停止。他说,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走过的10年,是了不起的10年,把长期以来被主流文化所鄙视、被贬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历史价值给挖掘出来了,提升到了民族精神的载体和原生文化宝库的地位,但时至今日是进行冷静科学反思的时候了。
“比如,前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申报工作,是在2005年至2009年全国非遗普查还没有进行或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一些深藏在民间的有重要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的项目,并未能进入非遗工作干部的视野之内,仍然沉睡在老百姓的记忆中。今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申报工作应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采录基础上……”
对于未来,刘锡诚表示:“在我余年的时间表上,民间文学的研究还会持续,至于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只有上帝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