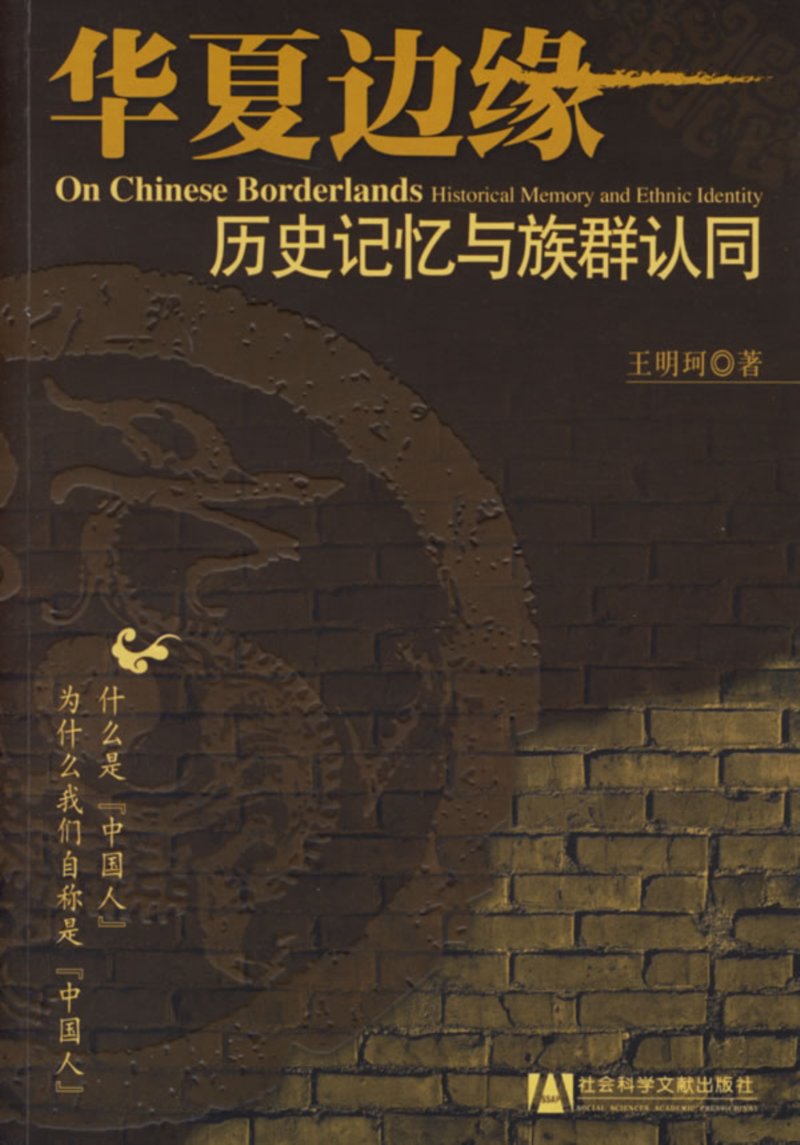什么是华夏的边缘——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一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整个汉文世界的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或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著作中,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精湛细部研究的著作称得上是凤毛麟角,而王明珂教授的《华夏边缘》却正是这样的作品。知道或了解华夏民族边缘的形成并非一个遥远而古老的知识,经过作者的描述我们才有恍然而悟的感觉。这种酣畅淋漓的论述所带来的震撼是最初阅读台湾允晨版时获得的。差不多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大陆读者有机会阅读这部著作。[1]
十九世纪以后,民族国家替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新的中国开始“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2]研究中国人的特质,从许多方面相继展开,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都基于同样基本预设来研究华夏民族源渊,即民族是一共有体质、语言、文化特征的人群。类似的假设,王明珂认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并不能成为构成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或充分条件。那么,和已有的研究假定对象是“中国人”转而描述“中国人”不同,作者要回答或要解决的问题的:“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或者说为何我们是中国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由此导入所谓“华夏边缘”的确立。作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图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图形。比喻虽然简单,却可以使我们一目了然,看到边缘研究取向的实质。
二
本书共有序论、十二章及结语,可分为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 Barth)的“族群理论”宣称: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边界”,而非包含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与文化特征论者所持有观点不同,一般来说,“族群”理论更趋向一种主观认同。围绕着认同是如何产生、变迁,产生了西方人类学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论:工具论和根基论。工具论者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变迁,而且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根基论者以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同根性”的基本情感,用此来凝聚所谓的同根人群。不过,他们并不强调生物传承或以客观文化特征来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释的传承。例如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非一定说他真是炎帝或黄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观认同(assumed)。
王明珂结合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与前述族群理论,调合工具论与根基论之矛盾。集体记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但这样,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所重建的“过去”本质如何。将某一族群的“历史”视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用这样的历史记忆凝聚一族群,无疑合乎根基论的判断;同时,它也在现实资源分享与竞争情境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修改、遗忘,以改变族群的边缘,如此说来这样也适合于工具论的观点。
基于以上对族群的了解和理解,作者提出一个不同于“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边缘研究”理论。“民族边缘研究”在方法上也与“民族溯源研究”有相当的差别:在考古学上,由注重器物之传播、演变转而注意人类的经济生态,以重建族群边界产生的资源生态背景;在文献上,将文献记载当作历史记忆,着重于分析历史记忆中所表达的“我群”与“他群”边缘分野及其变迁。沿着这个思路,结合人类学的历史学研究将使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族群现象有进一步的理解,这种理解也能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族群生活经验相互映证。
在古代的帝国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帝国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这当然与疆域辽阔有关,而地理单元的复杂性是形成帝国周边的基础。作者在第二部分说明华夏生成的背景,也就是华夏生态边界形成的过程。青海的河湟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和西辽河流域是其论述的重点,以考古资料说明,在这些龙山文化边缘地区的农业人群,如何因气候变迁而逐渐走向游牧化,尤其是专业游牧化道路的。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500-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深深地影响了北方人群的生态变化。在河湟地区,干冷的气候迫使齐家文化以后人们的经济生活,逐渐以养羊取代养猪。到了卡约文化时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700-600年或更晚),河湟居民已走向游牧,放弃了农业和定居生活,畜养了大量马、牛、羊等食草动物,为了便于移动迁徙,而少有大型器物转而偏好小型器物和装饰用品。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及辽西地区,在此气候条件下促使人们放弃原有的农业定居方式,采用粗放农作,畜养食草动物并经常性的移动。这样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南移至晋、陕、冀之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他们便是史书记载中的戎狄。南部的东周诸国,在此刺激下产生了一体的华夏意识,向北驱逐戎狄,扩土拓疆并建立长城以抵御他们。华夏向北扩张,建立长城保护中原资源,如此,更使长城以北习于畜牧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经济之中,专业游牧人群就此诞生。专业游牧化的产生与人类驯养食草动物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游牧化的经营策略在于,通过食草动物将人类不可以直接食用的草类,转化为肉、乳,以供人类直接消费;牵引力、皮毛等也可供人们使用。专业游牧化的形成,促使北方的族群关系发生巨大的转变,华夏民族认同得到空前的强化。作者所谓的“华夏边缘”便为视重视畜牧、不重农业、不定居并有武力倾向的混合经济人群为“异族”,北方族群“非我族类”的概念得以确立。由此,“华夏”也自认为是定居的,以农业经营为目标的,并且爱好和平的人群。长城的修筑,代表游牧、农业二元对立,华夏世界愿意积极保护农业资源区的极限,是一个折衷的选择。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国的建立,也是华夏族群边缘确定具体化的象征。
第三部分为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首先,“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是全书关键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国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个主题,周人是构成华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换言之,追寻周人族源,无疑是追溯华夏民族族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王明珂是以周人族源传说来说明华夏边缘的成长过程。前面考古所见的北方人类生态变迁,成为理解周人族源的叙事基础。《史记》中有关周人族源的说法被作者视为一种历史记忆文本,运用文本分析来探索产生此文本的情境。他指出,此文本强调的是周人与戎狄间的三种对立关系:即行农业与不行农业,定居与移徙,好和平与爱侵掠。因此,该文本产生的情境信息,必然是当时有些人群不经营农业,经常性地迁徙,并习惯用武力的方式进行掠夺。这些正是该书第二部分考古材料所见的,公元前1400年左右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的混合经济人群出现在晋陕北部高原、山地,并继续南侵。周人原出自混合经济人群——戎狄,但在他们与部分戎狄进入中原农业区,接着持续地向东扩张他们的势力以后,周人与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关系愈来愈呈疏远的态式。西周时期,姬周与戎之间仍若即若离,表现在姬、羌、赢(秦)、戎间的族群政治之间。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灭了西周之后,“戎”终于完全成为“异族”的代名词。周王朝东迁后,尊王攘夷的呼声高涨,北部各诸侯国纷纷驱戎,修建长城,表现出强烈的华夏认同感,华夏实质性的边界——长城的修筑,是用于保护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农业资源。这种强烈的宣告,终于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线。
秦人融入华夏后,更西方的人群被称为氐羌。王明珂用华夏的“羌人”概念来探索华夏边缘的西向漂移。与史学界的一般对古羌人的研究有些差别,王明珂并没有将“羌”视为一个在历史时空中迁徙的民族实体,而是将它看成是华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华夏的人”,也就是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缘。因此,分析文献中由殷商到汉代“羌”地理空间之漂移,也就是探索华夏族群西方边缘的扩张过程,这些内容是作者依据其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3]华夏边缘的扩张、推移,在本土层面上有赖于华夏边缘人群接受华夏祖先(历史记忆)因而成为华夏。现在的江南无疑是华夏,但是,吴国以前这里曾被华夏称为“荆蛮”。春秋时,句吴王室宣称其祖源为西周太王之子——太伯。太伯让位而奔于长江下游的吴,成为本地王,因而句吴为华夏之国,苏南人群也成功的华夏化。类似的例子,王明珂列举许多来说明华夏寻找失落的祖先后裔,与非华夏接受一个华夏祖先,促成华夏化及相应的华夏边缘扩张。
第四部分是大陆版与台湾允晨版不同的部分。作者用“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以及“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取代了允晨版中的“羌族历史记忆”和“台湾族群经验”两章。他在大陆版的序言中叙说了替代的原因,这是因为旧有的两章多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现在的研究则倾向于长远的历史观点,并以细微人群的互动关系,来理解近代中国民族形成。且当时他尚未完成羌族的田野研究,目下两章更能反映他的学术关系和见解。近数十年来,当代国家与国族主义研究中一直有“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前者在看待当代民族为一有长远历史的民族体;后者则视民族为近代想象的共同体与建构的产物。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一种能调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矛盾冲突的新说,以此来诠释当前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列强的全球边缘空间、资源争夺中,传统华夏边缘地区,也有被瓜分侵夺的危机。由于华夏边缘与华夏在历史过程中有密切的经济互动,且华夏与非华夏之间的边界相当模糊,因而近代中国国族在擎造之始,便将传统华夏与其边缘的部族聚为一整体国族。在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概念之下,民族被视为有共同语言、体质特征、文化内涵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因此,当时知识界的使命是,透过民族史、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等新兴学问的研究,在知识上完成民族及其边缘的再造。作者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早期民族调查研究为例,说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史语所的民族学者如何走入西南边疆,通过他们的调查研究将传统华夏心目中的南方与西南“蛮夷”,或汉与非汉族群边界模糊的各族群,识别、区分为各少数民族。史语所的学者也曾参与当时民国政府推动的“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命名”,用于消除有民族歧视意味的族称,表现出华夏边缘再造的改变。作者借史语所一位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物黎光明的边疆民族事业,来表现近代国族边疆再造的整体情境,以及许多个人如何用其知识、行动甚至生命来贡献国族边缘的再造之中。
在“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这一章中,作者借历史上四川西北部北川居民的汉与非汉族群认同变化,来说明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及这些认同变迁的微观社会过程。中国古文献有“禹兴于西羌”的说法,由秦汉到明清,这种历史记忆被许多华夏西部边缘人群用来强调其华夏认同。然而在此华夏边缘,自称汉人者仍被下游的人们认为是蛮子,他们也视上游的人群为蛮子。如此这样“一截骂一截”的歧视,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北川山区的民众都自称汉人,并且以本地为大禹故乡深感光荣。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及过去被视作“蛮子”的记忆忧在,先是最上游的村寨人群被识别为羌族。而后,自上而下许多山区居民都要求成为羌族,出现“一截攀一截”的情景。大禹则被诠释为羌族的祖先,成为川北羌族的认同符记。仅在川北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两千年来华夏边缘如此摆荡,本地山民被视为蛮子,成为汉人,又成为羌族,见证了近代民族概念下的少数民族化变迁,这只是长期华夏边缘宏观变迁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川北的例子也见证了汉化的微观情景,也就是在华夏边缘之亲近人群之间,人们相互歧视、夸耀、模仿、攀附,这样,许多人群逐渐融入汉民族当中。在这一章之中,王明珂用了一个比喻,就象一截燃烧的木杆,部分已碳化,另一部分则仍为木质,华夏边缘的微观情景便是正在燃烧的部分,从本质上来说这两部分仍是一个整体,从而变的密不可分。
本书的最后,作者用“资源竞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为叙述目标,结束讨论。他强调了本书在思考华夏边缘历史变迁的三项主轴,即资源竞争、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从理论层次,他说明了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下,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典范观点的社会记忆如何使得边缘的声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会边缘。因此,在学术上王明珂强调了注重多元因素,边缘及微观声音,也形成了对现实人群的关怀。
三
该书在许多层面上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尤其是在方法论、族群理论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和贡献。
1、本书对考古学、历史文献以及对人类社会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学方面,由于将华夏看作成一个维护共同资源的群体,产生于特定资源竞争环境当中,因而,在此议题当中王明珂强调生态与环境考古的重要性。在研究北方游牧社会文化的起源与形成方面,过去许多学者基本都是从器物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此类问题,例如斯基泰风格或北方系风格动物纹样等。作者则提醒考古学者这种以器物间的相似性(similarity)来建立起来的逻辑关系的模拟法,一但被滥用或过分依赖,都经常会造成伪知识。考古学中经常赖以维系的陶器变迁与社会政治变迁之间常常会缺乏一致性,并不能够可靠地构建器物分类与社会人群分类(socialgrouping)之间密切关连。考古学家经常宣称的一些考古学证据,来支持历史文献中的族群划分与人类迁移,实际是可质疑的。本书不但注重调整考古学的研究策略,更注重历史文献的解读。由动物中的猪、羊比例变化,居址中有无聚落形态,陶器的大小变化,生活工具(如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变迁等综合因素,来探讨游牧化这样的人类经济生态的演进。尤其在有关周人族渊(122-145页)和句吴王室的族源(163-184页)的探讨中,作者通过对“类比法”器物型态的质疑,精彩地阐述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联。认为考古资料之间或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间所呈现的“异例(anomaly)”,才是我们认识社会与历史本质的关键(144-145页)。
自从王国维倡导在上古史研究中使用所谓“二重证据法”以来,深受学界的追捧,被认为是研究古史的不二之法,有人甚至推衍成所谓“三重证据法”。本书对此却有稍稍不同的理解,当然这并非要否认“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而是让人们了解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另一面。他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看作是“二重遗存”,它们的制作保存,通常贯彻着某种意图,它有时传递的并非完全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主观的,有选择的历史。
2、全书对文献史料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记忆”。所谓的历史记忆分析也是一种文本分析,目标不在于厘清文本所陈述的是否为事实,而是从文本分析中探求书写者所处的情境,及其个人情感与特定意图。例如对《史记·周本纪》,对清代姜炳章《白草歌》,以及对黎光明的《川西民俗调查报》的分析,无不透露出这样的悬的。以《史记·周本纪》为例,传统史家钱穆曾经利用、参考这篇文献撰写了著名的《周初地理考》,[4]详细考证公刘的迁徙路线,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姑且不论司马迁所述或者钱穆所考是否为历史事实。同样一篇文献,经由本书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此历史记忆的叙事间,书写者表达了定居与迁徙,务农与不务农,和平与武力等等我群与他群的区分。这便是另一种历史事实,也许是一种更真实的史实,华夏形成时期资源竞争与人群认同的情景。
在人类社会研究方面,本书特意强调的“边缘与边界研究”,这是近年来愈来愈受到重视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视野。在本书的表现中,作者不只是用“边缘”来探讨华夏的形成与变迁,更在许多地方表达了边缘与边界研究的旨趣。将传统历史知识看作为“典范历史”,注重“边缘”和社会底层的多元声音。例如,关于中华民族边缘再造方面,他很少提及史语所傅斯年、李济等人的丰功伟业,却以大量篇幅介绍该所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黎光明的事迹。又如,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以四川偏远地区的北川人认同的历史变迁为例,用社会底层亲近人群间的互动来说明汉化的微观社会过程。
如果说作者在本书的写作策略上,以跨越游走于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人类学之间的倾向为期许的话,那么他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并不以本书为限,《羌在汉藏之间》和《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都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5]然而,尽管作者的人类学田野资料的调查、阐发、描述都达到使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折服的程度,[6]但他仍摆脱不了某些困惑。某些人类学家竟以学术训练背景为由,质疑他的人类学贡献。[7]这种过分拘泥以学科训练背景来区割研究者的作法,多少有点教条主义的倾向,也显得有些武断。我们当然应当尊重学术职业化以来所建立的学科模式,这是多少代学人努力的结果。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研究的范围、取向、方法,承担不同的学术职责,细密化的分工也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但这些并非一成不变,跨学科整合的愿望,是为了打破学科间生硬桎梏而达到的一种理想模式。王明珂的工作路线,恰好填充了考古学、历史学及人类学的方法上的罅隙。像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常规学科会压制新思想,新思想往往会破坏常规学科的基础承诺。非常规的研究就这样开始了,危机只有通过所谓的科学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是革命一旦成功,就产生新的范式,成为新的正统。科学的进步显然是循环的,常规科学是科学革命的前提,革命以后是常规,常规引起革命,如此往复。[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王明珂的研究,他模糊了原有的学科界线,甚至模糊了著作题材。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甚至是社会学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东西。但跨学科的结果并非原有学科知识算术级的增加,而是在创造一种新兴的研究模式,也许给以后跨学科研究提供某种典范。或许现阶段还无法证明这种预设,但我想这对王明珂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
2、作者是较早向汉语世界推介族群理论并有相当影响的学者之一,[9]并且将族群理论运用于具体研究实践之中。在族群理论方面,本书以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来发挥并补充巴斯以来的人类学族群理论与族群边缘研究,同时,用对亲近人群间之区分的微观研究(第十一与第十二章)来充实族群研究内涵。对亲近人群间的敌对与区分的微观研究,有清代川北同村寨或邻近村寨民众的互动,有民俗调查者黎光明与土司家人、喇嘛之间的互动。不过,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作者在《羌在汉藏之间》有关章节中有更清晰的表达。[10]当然,更重要的是,该书并非空谈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而是以华夏边缘的历史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研究中修正、补充这些理论,以促进我们对历史的过去和现实社会都有所了解。
3、基于这些方法和理论,王明珂可以说是对于“什么是中国人”或“中国人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之类的议题有一种新的诠释。它并非只是描述华夏的汉民族史,也不是描述一个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史。而是以“华夏边缘”的历史变迁来说明古代华夏到近代中国的深刻变化,并由此旁及“边缘”内外群体间的资源竞争、垄断、冲突以至于在当代民族概念下的再整合、分享的过程。或许,由于使用“华夏边缘”一词,作者常被误解为难以摆脱华夏或汉族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当我们认同中华民族在形成中“多元一体”的概念后,就不会纠缠在人数的多寡与地域资源的多少,谁是中心、谁是边缘,这些简约的数字关系之中。在新型的国家民族体制中,传统的汉族中心或边疆民族的异族观念都将被抛弃,这些对构建中华民族凝聚力都非常重要。因此,作者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关系历史与民族团结的新知体系。在这一新体系中,并不是要强化或者印证谁为主体、谁为边缘,而是让大家可以反思或反省为什么有这样的区隔,以及由过去到现在的演化。
4、另外,作者的社会学倾向实际表达出他对现实人群的关怀。此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对边缘人群的关怀,这样的边缘人群不只是少数民族,也是历史上的被统治者、社会底层民众与知识的边缘人。由结语的最后一节可以看出,作者对过去的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中的一些策略有所批评。他认为华夏认同的扩张,阻断了周边人群共享较丰富自然资源的机会。这样,在宏观历史上造成北方游牧部族不断入侵华夏帝国,南方与西方的非汉人群也因资源缺乏而经常性的处于纷扰动乱之中。当然,在微观社会层面,由歧视、夸耀、模仿、攀附而推进的汉化过程中,也孕含着许多被视为“蛮夷”人群的痛苦。与此相对,王明珂对由于西方民族概念引进后,近代变迁而形成的当代现状:华夏与其边缘合一形成的中华民族,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将这个看法更明确地带入《羌在汉藏之间》的结语之中:
在近代中国国族之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此地区长程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将广大东亚大陆生态体系中相依存的区域人群,结合在一资源共享之国家与国族内。[11]
在族群意识上,由被歧视的边疆蛮夷转变为当代以本民族为荣的少数民族,这也是近代民族边缘建构下的成就。从这个结果来看,作者以为晚清部分革命党精英准备建立一个纯汉族的民族国家,无疑是一种狭隘自利的想法。同样,由人类生态资源观点来比较欧亚大陆东西两半部分的体制,作者也较肯定东半部资源经整合而一体共享的中国体制;相反,西半部虽有沿大西洋沿岸少数富强而讲求自由的国家,但处于内陆诸国则因资源匮乏、品种单一而经常卷入由宗教、种族、阶级、性别而引发的战争与迫害之中。
然而,《华夏边缘》并不只是要肯定当前条件下的国族体制,更重要的是期盼人们在一种新的民族与历史知识下有所自省或反思,以调整当前,规划未来。譬如,该书对“汉化”的新知告诉我们,传统上以“夷狄入于华夏则华夏之”来说明汉人对外夷汉化的宽容性,这种看法至少是有相当缺陷的。从汉化的微观过程来观察,是亲近人群之间的相互歧视、模仿与攀附来推动汉化过程,此间,涉及到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扰与苦楚。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将之视为“汉人”对“蛮夷”的民族歧视,因为辱骂他人为“蛮子”的人群,经常自身亦被他人视为“蛮子”。更重要的是,将华夏边缘的形成、变迁置身于欧亚大陆东半部的人类资源竞争、冲突与共享的情境中来了解、理解,我们就更有理由调试、改善各民族间、地域、社会阶层人群间的各种差距。
四
作者在全书中将华夏民族完全等同于后来的汉族。汉民族的称谓由华夏——汉人过渡到汉族,恐怕实际上折射出汉民族的成长历程。最初的汉朝所说的“汉人”是一个与“秦人”相对的概念。有种族意味的“汉人”一词,是在十六国北朝时期逐渐酝酿产生的。由华夏到汉族,这之间发生了怎样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是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学的学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十六国北朝时期又是所谓“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大量非华夏的北方和西北民族进入中原,融入原来的华夏社会,其中相当多的家庭还进入社会主流,正如胡三省所感慨的,“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12]边缘进入了中心,夷狄变成了正统。原来的华夏中心(魏晋高门)避地江左之后被北朝斥为“岛夷”,随着北朝政治上的胜利而最终失去了其传统地位。这是一个中心流落到边缘的例证。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篇章,而且对于理解华夏民族的历史命运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那么,在作者的族群边缘构架中,如何动态地解释这一历史过程呢?相应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观察,这个过程并没有到隋唐时代完结,而是经由新的历史条件在宋辽金元乃至明清时代而继续着。本书没有就此展开讨论,甚至也没有给出必要的提示性思考,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另外,作者的华夏边缘研究由于强调族群认同的主导性,对国家或国家权力在华夏边缘形成过程中的主动干预未予讨论。事实上,整个国家权力机器在华夏边缘形成和固化中的能动作用是不应忽视的。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的领土的划分,同样也意味着空间上中心与边缘的对应。国家统治阶级、统治人群的存在也区隔了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与边缘。哪怕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国家也会动员很大的资源来确保核心与边缘结构的稳定。透过权力干预华夏边缘,使核心区域的文化渗透并改造边缘地区,此类例证很多。以本书讨论较多的汉朝为例,《汉书·循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载:
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历,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卖刀布蜀物,齐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3652页)
文翁通过职权“诱进”当地俊才赴京师,学习汉文化的各类文化、法律、制度,回到当地再普及汉文化,使之在边地畅行。既使对鞭长莫及的匈奴,也透过文化的渗透增加汉文化的影响力。《汉书·匈奴传》:“时,(王)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3819页)用利诱的方法,使匈奴单于放弃原有的多音节名字“囊知牙斯”改为单名“知”,强制匈奴接受汉人的单名制度。[13]
定期的朝贡、质子及婚媾、征战、讨伐还有动员军备、增加军费开支,在边缘地区进行行政整合,都是国家干预权的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凸现王朝或国家在其边缘凝聚了权力,运用强制性措施来防止边缘崩溃,给国家安全带来危机。也许作者认为这些讨论与本书的基本旨趣相左,虽然书中有时偶尔也会涉及帝国在掌控其边缘的政治理由或权力措施,但通常很快会一笔带过。
另外,大陆简体字版中或因手民之误,或因编辑、作者疏失出现一些错误。36页倒数第2行 “北京人民出版社”应为“人民出版社”,北京二字当属衍文,265页参考书目亦同;61页倒数第2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局”应为“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263页参考书目亦同;63页倒数第2行“青海文物管理局考古队”应为“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265页参考书目亦同;81页倒数第6行“《竺可桢全集》”应为“《竺可桢文集》”,265页参考书目亦同;110页倒数第3行“《辽海文物学刊》1933年第2期”,应为“《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267页参考书目亦同;122页倒数10行“《西周地理考》”应为《周初地理考》; 148页倒数第4行“联经出版社”应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65页参考书目亦同;149页倒数第8行“濒于赐支”,应为“滨于赐支”; 169页倒数第10 行“《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第6期”,应为“文《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第6辑”;193页倒数第2行“韩国汉籍民俗业书”应为“韩国汉籍民俗丛书”; 210页注释倒数第2行“沉松侨”应为“沈松侨”,264页参考书目亦同;228页倒数第1行“吴江沉氏世楷堂刊本”,应为“吴江沈氏世楷堂刊本”;260页参考书目17行“《中国考古学集刊》1989年第6集”,“中国”二字属衍文;263页参考书目1-2行“成都市,民族出版社”,似有误,四川民族出版社在成都,如是民族出版社则在北京;267页参考书目倒数第1行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缺出版年份;268页参考书目第5 行“1928年第1集”应为“1928年第1本第1分”。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1期。如文字有歧异,以发表者为准。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199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同名书的中文简体字版,相较前者后者有所改动,大陆版可视为作者《华夏边缘》的修订本。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为修订本,而与前者无涉。
[2]参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期,1997年12月,第5页。
[3]参见Ming-ke Wang,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ec Boundarie(Ph.D. ai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92)。
[4]参见钱穆《周初地理考》,原载《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后收入其《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5]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6]参见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序〈羌在汉藏之间〉》,页i-ii。
[7]参何翠萍书评《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汉学研究》,22卷1期,2004年。对于何氏书评中的一些批评,王明珂作答,见其《边界与反思——敬复何翠萍教授对拙著〈羌在汉藏之间〉的评论》,《汉学研究》,22卷1期,2004年。
[8]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48-100页。
[9]参见李亦园《评论进出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第431页。
[10]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 93-136页。王氏对西方理论渊源的讨论,见105-107页。
[11]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389页。
[12]《资治通鉴》卷一○八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29页。
[13]参见罗新《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2期,第30页。有理由相信是否给死去的匈奴单于号决定权在汉朝官员手里,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