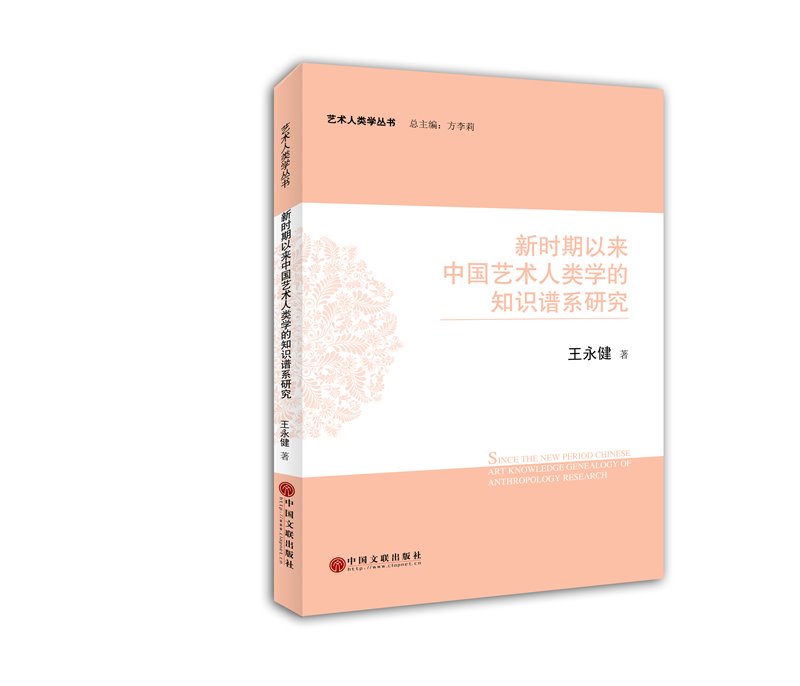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目 录
摘要 XVIII
绪 论 1
一、本论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1
二、选题意义 1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3
四、研究综述 4
第一章 学术准备时期:从文本到文本的学术研究 20
第一节 艺术人类学界说 20
一、艺术人类学的概念引入 20
二、艺术人类学的概念界定 21
三、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与研究对象 26
四、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28
五、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设置 31
六、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基础 33
第二节 国外译介及影响 40
一、格罗塞与《艺术的起源》41
二、哈登与《艺术的进化》45
三、拉德克里夫·布朗与《安达曼岛人》51
四、莱顿与《艺术人类学》54
第三节 原始艺术命题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57
一、问题的缘起 57
二、原始艺术命题研究的状况与特点 58
三、“原始艺术命题”研究兴盛的原因 65
第二章 学术起步时期:从本文到田野的学术转向 68
第一节 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 68
一、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背景 69
二、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70
三、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评价 76
第二节 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 77
一、人类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78
二、美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99
三、民俗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107
四、艺术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117
第三节 艺术人类学相关课题的研究 128
一、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 129
二、西部人文资源课题研究 131
三、本土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 142
四、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理论方法探论及其学科化建设 143
五、壮族艺术的人类学研究 146
六、晋北民间庙会中的仪式音乐班社研究 147
第四节 有意识地走向学术联合 148
第三章 稳健发展时期: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学术研究 150
第一节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及其学术研究 150
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 150
二、学会平台上的学术研究 151
三、学会成立以来的相关课题研究状况 156
第二节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157
一、译介工作的新发展 157
二、学科建设的稳步推进 159
三、人才培养的迅速发展 164
第三节 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类非遗保护研究 165
一、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类非遗关系释义 166
二、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艺术类非遗研究实践 167
三、艺术人类学对艺术类非遗研究与保护的价值与意义 175
第四节 本土化的理论与经验 176
一、“接通”历史与田野 177
二、美和审美权力的建构 182
三、“遗产资源论” 187
四、解读“我者”乡土社会 190
第四章 反思与展望 194
第一节 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194
一、译介工作亟待跟进 194
二、田野工作的反思 195
三、民族志书写方式的转变 200
四、学科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202
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新节点 203
一、城市艺术田野研究 203
二、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 217
结 语 230
一、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231
二、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33
参考文献 236
附录:中国艺术人类学大事年表 247
方李莉:序言:论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之路
王永健博士新完成的专著《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即将出版,我为他感到高兴。王永健曾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方向是艺术人类学,这部著作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的研究。为了研究这一论题,他花了三年读博士的时间,毕业后,在此基础上他又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后又努力了三年,前后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沉甸甸的专著。
这部专著的完成不仅是在他个人学术生涯中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其也意味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因为这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三十年来所完成的第一部学科史方面的专著,这一专著的完成,既是王永健博士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又是整个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王永健博士将他的这一研究定位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发展史的一个基础研究,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再研究”。”[1]如果没有三十年来学界的共同努力出版和发表了众多的学术成果,也就不存在他的这一研究和研究的最终成果,因为他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些前面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这部专著的出版既是王永健博士在学术上的一个转折,也是中国艺术人类学这一学科发展的一个转折,它说明了中国艺术人类学通过三十年的发展,终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王永健博士在这部专著中,将中国艺术人类学分为:“学术准备时期:从文本到文本的学术研究”;“学术起步时期:从本文到田野的学术转向”;“稳健发展时期: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学术研究”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准确和客观的。
人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传入中国有近百年的时间,伴随着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以人类学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艺术的学术成果就开始出现。但其真正成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引起学界的关注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所以作者将研究的时间起点定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也是相对准确的。作者认为,在第一个“学术准备时期”,“艺术人类学被介绍到国内,学界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关西方艺术人类学的著作,当时,国内围绕着“原始 艺术命题”兴起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热潮,他们主要关注艺术的发生学等相关问题,停留于纯 粹文本意义上的理论分析与阐释,这种学术传统持续时间很长,直到 1990 年代中期以后, 才陆续出现有意识地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亲历田野的实证研究。”[2]正因为如此,作者的主要笔墨主要是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所经历“学术起步时期”和“稳健发展时期”,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发生了从“文本”到“田野”研究的转向, 学者们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进入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就艺术事象展开实证研究。
但这样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呈现出的是一个多元性的发展态势,其研究的主力来自于哲学、美学、文艺学领域、不同艺术门类、 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领域的学者。[3]也正因为如此,作者要想从这么多不同的学科中理出一条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线索是很不容易的。于是,他在写作方式上为自己定下了几个原则,第一、写作的立意不在于包罗万象式的囊括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所有文本,做一个面面俱到的分析与论述,而是采取一种主题史的写作思路,通过 对大量研究著述的收集、统计与分析,挑选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学者及其团队的代表性文本作为分析和论述的对象。[4]第二、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 的学术研究领域,它的研究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作者对学术史的研究亦是建立在对该领域研究著述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 第三、统领课题的线索为: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和学界热点问题和关键学者及其“文本”。[5]由于把握了以上几个写作原则,使作者在纷乱中找到写作的主线,在主线中又能找到许多丰富的支流与写作文本,其才在我们面前呈现了这样一本既有理论性,又富有条理性和逻辑性的学术专著。
从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笔者开始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并第一次到达景德镇做有关传统陶瓷手艺人的田野考察,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正是王永健博士所论述的中国艺术人类学所经历的“学术起步时期”和“稳健发展时期”,所以笔者是这两个时期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所以笔者在这里所做的一些讨论,既是对王永健博士的这本专著的评述,也是对自己多年来的一些有关中国艺术人类学思考所形成的某些观点的总结与归纳。
一、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
“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是由费孝通先生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个词所转借过来的,这是1980年3月费孝通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奖的大会演讲题目。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学术界也一样充满着走向未来的热情与对过去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中,费先生说了如下的一段话:“我从正面的和反面的教育里深刻体会到当前世界上各族人民确实需要真正反映客观事实的社会科学知识来为他们实现一个和平、平等、繁荣的社会而服务,以人类社会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就有责任满足广大人民的这种迫切要求,建立起这样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6]他还说:“我立志要研究中国社会到今天已有五十年了,科学的、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研究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这就是我在题目中所说的人民的人类学的涵义。”[7]可以说,他的这一理想和这样的研究方式影响了中国的人类学,同样也影响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
在王永健的这部专著中,他首先关注到了费孝通先生对艺术人类学发展的思考,并拿出了一节的篇幅来论述费孝通先生的艺术人类学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中国艺术人类学能够走到今天与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费孝通先生在晚年,从早年关注的“志在富民”开始转向关注“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早年他关注“志在富民”是希望中国人能摆脱贫困,到晚年他关注的是中国人“富了”以后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所以他说:“我所致力的还只是要帮助老百姓们吃饱穿暖,不要让他们饥了寒了,这一点我可以体会得到。但再高一层次的要求,也就是美好的生活,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我就说不清楚了。但我能感觉得到,所以要把它讲出来,而且把它抓住,尽力推动人类的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就是向艺术的境界发展。”[8]他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向“艺术境界发展”的“艺术化的生活”。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才可以担负此任。所以,老先生关心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也首先是从关心人民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的,这与他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目标和理想是一致的。现在回想费孝通先生的确是高瞻远瞩,他所说的,社会将会进一步向艺术的境界发展,因此,艺术化的生活会成为未来人们努力追求的方向,在今天的确出现了,在笔者也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文章中提出了“审美性的现代化”[9]的问题,并认为,“审美性的现代化几乎成为了后工业社会的某种标志,而审美日常生活化也成为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工作者热衷的话题。”[10]笔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也是在景德镇和798及宋庄的田野考察中意识到的。但回想起来,费孝通早在十几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另外,针对这一问题,他还谈到:“我们现在应当讲的还是科技,是讲科技兴国。但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能要文艺兴国了,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11]当今,费先生提到的“文艺复兴”现象现在也已经出现,近年来笔者以及笔者带领的课题组在考察中,已经看到全国许多地方如景德镇、宜兴、镇湖、莆田等都已经出现手工艺复兴的现象,而且这种复兴并不仅仅是由当地艺人所主导的,而是由许多外来的年轻的艺术家们与当地艺人共同主导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具有艺术象征符号的手工艺品具有广泛的市场,也就是说,在民间人们正在利用艺术符号复兴中国的传统艺术。笔者认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并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重新挖掘我们传统中的有用基因,在当代的土壤中培育出新的文化。”[12]
费先生还说:“现在我们人类的文化要发挥精神上的享受,发挥情绪上的感动,朝着这条路线走,最终还是要走到一个艺术的世界里去,这就是人类最终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人类文化的最后导向,导向美好世界的追求,这也就是你们艺术家要出的力量,要指导文化的发展。”[13]在这里他向艺术家提出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参与社会导向美好世界的追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当今的社会,艺术家不再只是一个远离社会进行独立创作的群体,许多艺术家都在积极地参与新的社会建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出现了新的艺术区。这些艺术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还带动了其所在地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不仅如此,还有许多艺术家参与了美丽乡村和小城镇的建设。以上的这些现象都需要有学者参与并进行研究和梳理,为国家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和新的理论框架,如果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学者们参与了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田野考察,我们就是进入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研究道路。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天我们对费孝通先生的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梳理是非常重要的,其让我们看到,由于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引领,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一开始走的就是“从实求知”的田野之路,走的是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之路。
二、田野工作中的艺术人类学
王永健博士在书中定义,中国艺术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属于“学术准备时期”。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时期集中研究的是原始艺术,探讨的还是艺术的本质和起源问题。这样的研究造成两个学术现象:第一,与国际人类学界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脱节;第二,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是从文献到文献的空对空的研究,并未走向田野。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没有田野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人类学的存在。所以,王永健博士将中国艺术人类学起步时期定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其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出现了一股进入艺术发生的本土现场,在社会具体的情境中研究艺术的潮流。于是,艺术学发展终于在20世纪末走出了书斋之内空对空的研究,而走上了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与省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由此成为最具活力的研究艺术的方法之一。[14]21世纪初出版的项阳的《山西乐户研究》,薛艺兵的《神圣的娱乐》,傅谨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田野考察》,方李莉的《景德镇民窑》、《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王杰文的《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张士闪的《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等,都属于这一学术思潮的产物。
可以说,从生活的整体出发,在具体的生活语境中解释社会事实,在现实问题中解读生活流动的本质等“田野转向”的研究方法,一举打破了新时期以来主体性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局限,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15]也由此,艺术人类学从一个来自西方的跨学科分支开始走进了中国学者的具体研究实践,受到了人类学、艺术学、美学及各门类艺术研究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了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因为学术研究需要有共同体。这一共同体除了大家共同研究的对象是艺术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田野工作的方法来研究艺术。
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章程中写道:“学会的宗旨是广泛团结和联络全国艺术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开展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注重实地的田野考察……[16]注重“田野考察和理论联系实际”,并以此来认识和宏扬“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正因为如此,学会的一些主要学术带头人不仅自己勤于做田野调查,还带领自己的学术团队,深入田野。如笔者的团队、王杰团队;王建民团队,洛秦团队,色音团队,杨民康团队,何明团队,麻国庆团队等。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之外,还有不少学会以外的学者团队也在做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如彭兆荣团队,徐新建团队,项阳团队等等,这些学者不仅是研究者同时也都是教授,他们不仅自己做研究还指导学生做研究,同时也都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带头申报相关的国家重点、重大课题,带领自己本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一起做。有关这些由不同学科带头人带领的学术团队所完成的田野成果,在王永健博士的这本专著中都得到了很好的梳理。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是在田野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在田野中取得自己理论成果的一个学术领域。
对于艺术人类学来讲,田野的重要性在于其艺术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当代的中国艺术理论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是在18世纪以后受西方美学思想主导而形成的理论系统,虽然近代有所变革,但毕竟不能取代中国自身的艺术学理论。要建立一套中国自身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艺术学理论,笔者认为,不仅需要有艺术人类学的参与,更需要有大量的艺术民族志来呈现各类的中国艺术现象。我们要尽可能多的知道,中国的艺术和社会建构,以及中国的政治国体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等等之间的关系,这些广泛的社会事实是超越个人意志的事实,只有我们弄清楚了在这些社会事实中艺术的坐标以及艺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真正说清楚中国艺术的全貌,同时也才能真正地认识到中国艺术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也是中国的艺术自觉,没有这种艺术自觉就不可能建立原创式的中国艺术学理论。
而且,笔者认为,作为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共同体,我们需要一支基本的学者队伍担当起艺术民族志的事业。如果我们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不能提供大家所关注的社会语境中的中国艺术的一些基本事实和面貌,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语境中的中国艺术的一些基本事实和面貌”不太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话,我们的学术群体就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练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同时,如果没有艺术民族志,没有艺术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艺术人类学领域中的扩散,就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艺术的图像,难以使我们在社会过程中理解艺术与人、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因此,中国艺术人类学不仅是在近二十年的田野工作中得到发展和成长,也是在不断地撰写艺术民族志的过程中求得新的理论建构。尽管如此,中国艺术民族志的撰写方法仍然有待于完善及进一步探讨,其中包括艺术田野和艺术民族志的关系,艺术民族志与艺术人类学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等等。
三、社会发展中的艺术人类学
由于中国的艺术人类学首先是在田野中的艺术人类学,因此,其所关注的不仅是艺术的本身,还包括了在艺术发生现场中的一系列与艺术相关的社会实践与社会事实,还常常会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理解中国社会的当代发展及变迁等。
如由费孝通先生亲自指导的,笔者当时牵头的,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西部多所院校的一百多位学者共同参与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课题下设:民俗、人文地理、文物考古、民间建筑、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戏曲、民间舞蹈等字课题组,这些课题组的成员们历时7年时间,做了大量的民间艺术的考察与个案研究。如:笔者的“小程村民间艺术考察记”、“陈炉镇民间陶瓷考察”、“安塞的剪纸与农民画考察”,胡晶莹的“陕北民间舞蹈考察报告”,杨阳的“敲打声中的虔诚之心——西藏藏族民间金属工匠采访报告”,刘文峰的“合阳跳戏――宋金杂剧的遗响”,曹娅丽的“藏族仪式剧《公保多吉听法》的流传与演变的调查报告”,何玉人的“渭南剧种剧团生存状态成因调查报告”,王宁宇的“我所触摸到的陕西传统乡俗刺绣”,杨萍的“凤翔泥塑当代变迁的考察与研究”,董波的“仪式、剧场与社群——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呼图克沁”仪式展演考察报告”等,这些艺术人类学的个案研究都是紧贴当时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再现了在当时社会变迁下民间艺术的重构与再生产的状况。也是在这些众多来自现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上,课题组完成了由笔者主编的《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总报告书》。后来笔者将这一理论成果进一步深化,完成了《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遗产资源论问题的提出》两篇论文。这样的研究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一种人文资源,重构了当代的中国文化,同时又为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了可以利用和开发的资源,从而让我们看到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互动和互为转化的一对辩证体。这样的研究,为当时如何解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所遇到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
像这样紧跟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动态研究,在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中还有许多,在王永健博士的这部专著中也列举了许多,如:张振涛的《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影戏箭杆王:皮影戏表演大师齐永衡口述史》、高星的《中国乡土手工艺》 ,安丽哲的《符号·性别·遗产:苗族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黄静华的《乡民的艺术人生——以艺人为中心的民间艺术考察和研究》、罗彬的《一个土家“端公”和他的傩仪面具》、张士闪的《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薛艺兵的《冀中乡村乐社的音乐祭礼》、魏美仙的《他者凝 视中的艺术生成——沐村旅游展演艺术建构的人类学考察》、《多重语境中的花腰傣服饰——以大沐浴为例的人类学解读》、邢莉的《蒙古族敖包祭祀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以2006年5月13日乌审旗敖包祭祀为个案》等等。[17]这些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中所得到的传承、发展与变迁的过程。而这些所谓传统的民间艺术在当今社会多数都被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此,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也就和国家目前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了某些非常重要的合流之处。
人类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是有历史渊源的。在人类学的历史上,美国和英国人类学界就有这样一个广泛共识,即“传统文化知识在与西方殖民化和全球化的遭遇当中正在丧失。人类学家以进入到田野中去“抢救”传统文化的最后遗产来作出应对。”[18]而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和米歇尔·费彻尔(Michael Fischer)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已发展起来的科学,其主要动机就是抢救文化多样性。民族志学者能够捕捉住变迁中的文化的真实,因此它们就可以成为人类学伟大的文化比较计划的原始记录”。[19]所以说,人类学从其产生以来,就关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并自觉地把抢救和记录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就是由不少人类学家发起和参与起草的。
而作为艺术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在我国已经宣布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中,超过80%是被作为艺术的形式被加以认定的,这些融入传统生活的民间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技巧和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20]因此,王永健在该著的第三章,专门拿出一节来讨论“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类非遗保护”的关系,他认为,“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引入到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中,使其成为这一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是非常有必要的。”[21]
而且他还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对田野点进行多次回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变化做到持续追踪考察。”[22]在这一点上,笔者深有体会,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艺的研究,至今已有20多年,其间笔者持续不断地回访研究。因此,亲历了其从仿古,到新工艺的出现,到外来艺术家和当地传统手工艺合作全面复兴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艺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对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和总结,得出了“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作为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离我们而远去,相反,其在帮助我们建构着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同时,还在帮助着我们看到通往人类社会未来之路。”[23]的结论。
另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来认定的表演艺术,大都是仪式中的艺术,对此,人类学家特纳提出一个社会剧场的概念,他认为,这些文化中的仪式就是表演;并不是说“仪式像表演”[24]。还有的人类学家将民间的仪式看成是文化表演,并认为“文化表演方法一直在鼓励将‘表演’视为一个整体,即,注重的不仅是表演的地点、风格和文本,而且还有观众、演员及其他人。”[25]这样的研究就有别于一般的艺术研究,因为艺术研究往往只是关注艺术的本身,而不是其整体的文化语境。
笔者认为,人类学对艺术研究的贡献就是研究者不再把艺术看成是纯粹的艺术,而是将其看成是文化表演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艺术是社会的表达形式,是文化的可视性展演,也由此可以认为,社会剧场,文化是脚本,艺术就是在剧场中的具体展演的形式与内容。因此离开社会的构成和文化的内容去空谈艺术是很难有完整认识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艺术是社会剧场中的艺术,是文化空间中的艺术,我们只有将其嵌入其中才能真正的将其整体描述清楚。
也为此,在每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年会上,总是有一个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论坛,讨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样的讨论,其焦点不仅仅是停留在保护,也涉及到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因为,对于人类学来讲,一种健康的族群文化从来不是一份被消极接受的来自过去的遗产,而显示了共同体成员的创造性参与……[26]。因此,在讨论中学者们不仅关心的是保护与传承的问题,还关心民众的创造性参与的问题,这就更使其研究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不仅是“从遗产到资源”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些遗产资源如何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新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最重要的再生文化之一。
也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与北戴河区政府、宋庄树美术馆合作,每年在北戴河召开一次“北戴河艺术论坛”,专题讨论艺术家如何参与美丽乡村及小城镇建设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应该从何种角度,帮助艺术家认识、保护、传承和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艺术人类学是以考察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切入社会,并以此研究来推动社会发展的。
四、国际交流中的艺术人类学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而中国学者要进入这一学科,首先就得弄清楚这门学科的来龙去脉,包括它的学科来源,理论框架,学科术语,学科规范等。因此,这门学科最初是从翻译和阅读西方文献开始的,最早翻译到中国来的与艺术人类学相关的著作是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紧接着是博厄斯的《原始艺术》,是198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类著作翻译出版时,正是学术界出现“原始艺术”研究热的时候,说明学界的翻译都是和当时的学术思潮有关。1991年翻译出版了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这部著作实际上讨论的也是原始部落的艺术,但内容有所改变。如果说,前面的那些著作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品、艺术风格和技巧的话,后者却更关注艺术与政治、艺术与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互动等。记得,笔者第一次看到这部著作时,正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这部著作的出现,激起了笔者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兴趣。但当时笔者的田野点不在少数民族地区,而是在景德镇这样一座传统的手工艺城市,因此,当时莱顿教授的著作以及翻译过来的系列的研究原始艺术的著作,对自己的研究的实用性不是太大,反而是从其他更接近当代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著作里得到的启发更大。于是,觉得急需要翻译一批更新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著作,才会促进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进步。2008年笔者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购买了一批最新出版的艺术人类学著作,带回所里让大家共同阅读并翻译,并让李修建博士利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所里的平台组织大家一起翻译,随后李修建博士又在国家图书馆查找了一批西方的艺术人类学著作和论文。通过几年的共同努力,不仅翻译出了许多西方艺术人类学的专著和论文,同时,联络上了莱顿教授、范丹姆教授等在西方颇具影响力的艺术人类学学者,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为学会年会的积极参与者。在莱顿教授和范丹姆教授的介绍下,笔者还与澳大利亚的墨菲教授,挪威的施奈德教授,维也纳的托马斯教授等有所联系,并保持书信往来。2014年在莱顿教授的推荐下,笔者曾到杜伦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并被该校的高级研究院聘为高级研究员,在那里做了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工作。
通过和罗伯特·莱顿教授的交往,笔者了解到,莱顿教授之所以对艺术人类学感兴趣,是因为其在伦敦大学学院读人类学本科学位期间,他的妹妹正在把艺术史作为她选择考试的学科之一,她要求莱顿教授在考试之前测试她的知识。令莱顿教授震惊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在他读硕士研究生的时侯,他与教他人类学课程的讲师彼得·乌克(Peter Ucko)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法国和西班牙上古代石器时代的岩画艺术的专著,并加入了彼得率领的史前艺术考察队。攻读完博士学位后,他作为一名初级讲师留在了伦敦大学学院教书,此时,彼得邀请他共同教授本科课程,然后,将这门课程称为“原始艺术”。一年之后,他们同意改名为“艺术人类学”。后来,莱顿教授根据这一讲义,完成了《艺术人类学》这部著作,该著出版于1981年,可以说是第一部冠以艺术人类学的名称写就的专著。当然,笔者在图书馆还查到过一本出版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的艺术人类学论文集,但不是专著,也就是说莱顿教授是西方最早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先驱。从2009年开始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年会,并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聘为高端外国专家,和该所的学者一起做了三年的研究,主要是和笔者一起指导研究生们考察景德镇。也由此,我们有了和西方艺术人类学家一起做田野的经验,并从中学习到了许多重要的田野工作方法。
经过翻译、阅读,以及与国外学者们面对面的交流,目前我们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知识来源,理论框架,前沿问题等都有了一个较清晰的认识。范丹姆教授的一篇文章《风格、文化价值和挪用:西方艺术人类学历史中的三种范式》,通过西方人对芳族雕像研究的三种范式,非常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历程。第一阶段是“比例和结构细节”,主要注重的是对艺术品本身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形式和价值”:将艺术嵌入到具体的文化空间中做研究,关注的是艺术与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个阶段是“挪用和价值创造”,研究的是离开原有文化空间后的艺术作品的价值挪用与再造,是对芳族雕像的后殖民研究。就目前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来说,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较多,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以及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是第三个阶段的更多。而且由于城市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我们用第三个阶段的理论更能解释我们今天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将会在下面的一个部分中谈到。
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对外交流及外译学术著作方面,王永健在其专著中做了非常详细和重要的描述,甚至还访谈了最早翻译莱顿教授的《艺术人类学》著作的靳大成研究员[27],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
五、理论建构中的艺术人类学
虽然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外来的学科,需要我们去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相关理论,但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国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如果只是照搬西方理论,而忽视本土的经验和本土的理论,就会形成学术上的教条。因此,王永健博士在其专著中,专门拿出一节来讨论这一问题,他在梳理了中国艺术人类学近三十年的学术文献后,总结了四条本土理论和本土经验。
第一、是“接通历史与田野”,这是项阳研究员通过长期在田野中考察和在古文献中查找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做艺术人类学研究与西方人类学家在原始部落做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献资料的文明古国,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做切片式的共时性研究,就很难理清楚文化语境以及艺术发展的历史演化脉络,只是以当下的现象下论断,很可能会是片面的,不够准确的。在这里笔者想到了费孝通先生当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讲座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前几天你们这里的乔建中先生,送给了我一本书,叫“土地与歌”,他是西北人,他在书中写到了“花儿”、“信天游”,他是你们这儿研究音乐的专家,学术带头人,他把现在还存在的民间的音乐,一直理到历史上的《诗经》,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从诗经到信天游,这是民间的一个大矿场。”[28]如果当时乔建中先生的研究只有当下的民歌收集,而没有涉及到讲清楚其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笔者相信费孝通先生对他的研究是不会有如此大的兴趣的。因此,接通历史与田野可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人类学理论。
第二、“美和审美权力的建构”,这一理论是王永健博士根据周星教授《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从政治宣传画到旅游商品——户县农民画:一种艺术“传统”的创造与再生产》和日本学者菅丰《中国的根艺创造运动——生成资源之“美”的本质与建构》等案例研究总结出来的。如果把研究的时间拉长,就可以看到,在历史上,中国的艺术向来与政治的权力密切相关,其艺术大都是为“成教化,助人伦”服务的,而且任何的审美都不是任意的,其是有价值体系和权力建构的,所以清代的顾炎武曾写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29]。其意思是所有的器物都承载着文化的意义,都不是单纯物质的“器”,同样审美也是一套文化的象征体系。既然审美是建构的,这里面就涉及到谁能掌握建构的权力问题,这些权力的拥有者可以是政府、学术精英、市场等等。但这些权力是如何运用或被运用的等等,这里面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空间。
第三、“遗产资源论”,这是笔者通过西部和景德镇的田野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其理论来源除田野考察之外,还受到费孝通先生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以及萨林斯的“在后期资本主义时期传统与现代不再对立”的观点的影响。笔者认为,之所以在后现代社会,会出现传统不再与现代对立的现象,是因为传统成为了再造新的文化与经济的资源或资本,在以原有的文化再造新的文化价值的今天,传统焕发出了新的青春。但这样的转化过程是以艺术为媒介呈现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化产业都与艺术的再生产有关,与生活的艺术化有关。艺术既是一种审美系统,也是一种教育系统,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是通过艺术审美的本土转化来实践的,而且这种实践的过程也是一种再教育的过程。这样的一些社会现象,需要用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和方法去理解它,并总结出新的理论,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解读“我者”乡土社会,这是王永健博士在其专著中总结的另一个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本土理论。“我者”这个词,最早笔者是在洛秦教授的文章中看到的,这是相对于西方人类学“他者”的概念提出来的。这也正是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研究角度的差别,对于西方人类学来讲,田野是在遥远的“异邦”,在田野中所面对的都是与自己文化相异的“他者”。但中国人类学家面对的田野就不一样,直到今天,中国人类学家的研究还大多是本国、本土的文化。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是为了研究自身以外的“异文化”,而中国人类学家则是为了研究自身以内的“本帮”文化,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是称作“我者”的研究。尤其是从费孝通先生开始,许多中国人类学家还是在研究自己的家乡文化,因此,被称之为“家乡人类学”。像这样“我者”的文化和西方“他者”的文化有何区别?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中国人类学和西方人类学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不仅是研究对象上的区别,最重要的还是研究目标的不一样。西方研究“他者”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把远方的“异文化”作为反射自己文化的镜子,而中国人类学研究“我者”的文化,是为了了解自身文化的来龙去脉及构成形式,以促进自身社会发展的进步。
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也一样,其实希望从艺术的角度来剖析和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构成与变迁。如薛艺兵的专著《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研究》,就是通过对中国五个不同地区五种不同类型的乡村民间祭礼及其音乐的个案研究,来理解音乐结构及祭祀群社会结构方面的同构关系,不仅提出了中国民间音乐祭礼的类型理论,同时也从这样的角度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构成有了更深的理解。笔者在《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的研究中,也力图通过对因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而形成的陶瓷手艺人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剖析来解读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同时又通过对其发展的变迁过程来讨论,这种传统的组织形式又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得到重构并发展出新的生命力的等问题。张士闪的《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也是以“小章竹马的祭祀活动”为案例,“重新认识、理解和复原乡民艺术背后的生动鲜活的民间传统”,并以此来探讨近现代华北地区社会变迁中村落艺术传统的形成与保持的问题。杨民康的“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研究,也是通过艺术研究来解读乡土社会的一个研究案例。
六、未来的展望与思考
王永健博士除对以上四个方面的总结外,还关注到了有关“城市艺术田野”的问题,将其看成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一个新节点。笔者深有同感,并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有关城市艺术田野的研究可能会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一个最前沿,又最具创新点的研究范畴。而且这一研究与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最前沿研究“挪用和价值创造”,“艺术的后殖民研究”可以有某些呼应。其具有的共同时代感就是,以往的“原始的”、“乡土的”艺术,已经在离开他们的本乡本土,进入了本国的或者异国的大城市,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家的,中产家庭中所喜爱的艺术品。当这些“原始的”、“乡土的”艺术到了异地异国的大城市以后,人们忘记了其原有的文化意义,成为了“真正”的“原始艺术”“乡土艺术”,从而实现了新的价值创造。不同点是,西方艺术人类学关注的是那些来自非洲的,大洋洲、美洲大陆的“第四世界”(由原始部落转化成的民族国家)的艺术在西方世界的价值挪用与再造,里面具有后殖民化的趋势。
但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又有所不同,30年前中国人口的89%生活在乡村,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民。但今天,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据统计,在2011年时就达到了51%,[30]也就是说,今天许多的中国农民已经成为了城市里的人。因此,如果说以往中国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村问题,今天最重要的则是如何将城乡问题化成一个整体,来全面地重新认识。就艺术而言,一方面是全球化引起的地方性反弹,让许多的乡土文化和乡土艺术得以复兴,这种复兴不仅出现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在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城市的一些商场、画廊陈设着一些来自陕西、云南、贵州等地的工艺美术品或绘画与雕塑,还可以在一些饭店、歌舞厅看到来自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歌舞。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深入进行,代表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转化为重塑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文含义的“遗产资源”[31],而这些“遗产资源”正是以往活跃在城市和乡村的传统民间艺术,当这些民间艺术开始成为城市艺术的一部分时,作为艺术人类学者的我们应该如何去重新认识它们?这些来自乡村的艺人、艺术家们是在为谁创作这些艺术?这些艺术有些什么样的新的表达方式?在这些艺术流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文化生态链?它们会给当代人的生活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其又将会如何与当代的艺术家们产生互动,而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艺术风尚和城市景观?同时通过这些传统民间艺术的价值再造,对中国的新的文化在生产带来哪些新的活力?等等。
任何新的理论都是来自于新的社会实践,中国这三十年的巨大变化,为中国学术理论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源,尤其是艺术人类学,因为艺术的理论往往具有先锋性,其所具有的创造性精神往往是冲破旧的藩篱的一种力量。但所有的这些理论创新都必须来自于社会提供的最新的和最鲜活的材料。因此,艺术人类学的田野材料是所有理论创新的基础。相信,通过学者们的努力,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会不断地得到完善,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发展也会汇集为一股推动中国学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读完王永健博士写完的这部专著,心中甚感欣慰,其让我看到了新的一代学人正在成长,也看到了他的勤奋与努力。全书收集了从20世纪八十年初至今的大多数与艺术人类学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进行了精心地梳理。在书的后面还附了一份中国艺术人类学大事年表,在这一年表中列入了从1981年至今,出版的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相关的重要著作,相关的重要国家课题,举办的重要学术活动等。通过这一年表我们一目了然的看到:在第一个十年,艺术人类学发展相对缓慢,成果也相对较少,但到第二个十年,成果开始丰富起来,国家课题也在增多;到第三个十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开始出现了加速度的发展,出版的成果,所承担的国家课题,所举办的相关研讨会都越来越多,其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轨迹,也让我们看到了王永健博士为了这一研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不仅是一项要付出思考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需要付出耐力和时间的工作。在此,我向王永健博士表示致敬!
这篇文章,既是为王永健博士即将出版的专著写一篇序言,一篇评述,也是笔者自己趁这一个机会,谈论一下自己对中国艺术人类学三十年发展之路中的一些看法。
[1]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2页。
[2]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3]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8页。
[4]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3页。
[5]同上。
[6]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第109-114页。
[7]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第109-114页。
[8]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岳麓书社,2005年第11页。
[9]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
[10]同上。
[11]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岳麓书社,2005年第11页。
[12]方李莉《生态文明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民政协报,2016年6月27日第10版。
[13]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岳麓书社,2005年第11页。
[14]张士闪《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学科景观》载于方李莉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十年精选读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版。
[15]同上。
[16]《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章程》,引自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网站http://www.artanthropology.com/default.aspx。
[17]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18][美]杰里·D·穆尔著《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4页。
[19]George E. Marcus and Michael M.J.Fischer.1986:24.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164页。
[21]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165页。
[22]同上。
[23]方李莉《论“非遗”的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
[24]Victor Turner, 1985b:180-181.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In On the Edge of Bush. E. Turner, ed. Pp. 177-204.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5]麦克尔·赫兹菲尔德著,刘珩、石毅、李昌银等译:《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26]Edward Sapir. 1968c:321. Culture, Genuine and Spurious.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Pp. 308-3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7]王永健、靳大成《走进艺术人类学:兼论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潮——靳大成研究员访谈录》,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7年第1期。
[28]方李莉《费孝通晚年思想录》,岳麓书社,2005年,第11页。
[29]清·顾炎武:《日之录》卷一《形而下者为之器》。
[30]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31]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
后 记
当我坐在桌前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书稿已到了即将出版的时刻,回想起七年前的考博之旅,一切皆历历在目。2010年,我参加工作已满四年,尽管工作已非常稳定,但我内心对进一步深造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这一年,我做出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先生“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然而,第一年的考试我并没有取得成功,先生不但没有放弃我,反而宽慰我可以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再多读一些书,夯实基础明年再战,第二年我如愿考入先生门下。岁月荏苒,三年的求学时光竟在恍惚之间攸然而逝。当我面对人生中最后一次以学生身份的毕业,对校园生活的留恋之情油然而生,感慨的话、感谢的人,很多很多......三年博士的学习生活,由衷感谢我的授业恩师,方师治学严谨,勤奋刻苦,经常是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便起床写东西,这种学术精神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无不敬佩,也为自己所做之不够而感到汗颜。在我求学的三年中,方师对学生的求知之心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经常会一大早六、七点钟便会给学生打电话来谈前一天所提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每每这个时候,做学生的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这本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在方师的精心指导下拟定的,当初的设想是艺术人类学作为引自西方的一门学问,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形成自己完备的学科体系,也没有对学科发展史做系统梳理的著述。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厘清三十年来中外艺术人类学学术发展历程,就显得尤为迫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罗易扉师姐和我拿到了各自的选题,罗师姐负责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思潮,我则主要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当我第一次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真有些手足无措,三十年学科发展的进程中,优秀的艺术人类学家辈出,是否有能力做出全面而充分的论述,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又是方师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动力,她经常鼓励我,时刻关心着论文的进展情况,每次见面必与我讨论文章的写作情况,从整体构思、框架结构,到逻辑顺序、重点人物和事件的选取,无不关照,我的写作思路也在这样的师生互动中慢慢打开、顺利推进。
学术史的写作不易,需要阅读大量的著述资料,将其消化吸收之后转化为自己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的评述。客观而言,这一过程是有难度的,我总在写出来又不断推翻的过程中挣扎。好在一路走来有众多师友帮忙,有了今天这本书的呈现。感谢刘锡诚老先生,虽已是80岁耄耋之年,但仍耐心地帮我梳理思路、寻找资料,每每我有问题请教,老先生都会热情地给予解答和分析,丝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极具长者风范。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心峰先生,在我论文开题及写作的过程中,多次提点和帮助;我爱人考入李先生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亲耳聆听先生讲学,尤其是他主办的艺术学“席明纳”(Seminar)更让我受益匪浅,这是一种开放式的学术讨论会,大家三五落座,对各自研究中的困惑和新发现,各抒己见、互相提问,许多问题就在讨论和争辩中迎刃而解。感谢远在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先生,在写作中遇到困惑时,我都会给先生发去邮件,先生总会在第一时间给予我鼓励和指导意见;先生来国内讲座和开会的间隙,我也总能得到先生的现场指教,这样无私的帮助让我十分感动。感谢薛艺兵、欧建平、王端廷、王列生、孙玉明、苑利、色音、彭兆荣、徐新建、李修建、安丽哲等诸位师友在开题、总结检查和答辩过程中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胡小满教授,从我2004年投到他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到我参加工作,再到博士毕业,十年的时间里他视我如子,在各方面无不给予莫大的关怀和支持。感谢同门兄弟姐妹和博士同班好友对我的帮助与支持,在这个集体里,我倍感温馨和幸福。
博士毕业后我有幸留院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宽松的治学环境和良好的学术氛围给了我后续发展的动力,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中,也使我能够有机会向身边的师友请教与讨论问题。工作一年后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了2015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在竞争十分激烈的评选中有幸获得了立项资助。课题立项后,我对原初的框架结构做了调整,增补了很多新内容,拓宽了研究的范畴,并力图在理论上有所推进。通过前后六年时间的努力,完成了该著的写作,这本书基本上呈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希望它能够对学科建设有所贡献,也能够成为一本进入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性著作。
到了该为这项研究画上句号的时候,读博的三年,对家人满怀愧歉,身为人父、子、婿,未能对孩子多一些关爱,亦未能为双方父母多尽几分孝道,反倒是他们经常在经济上给我以支持,并帮着照看家庭。爱妻秦佩,从考博到现在她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事无巨细,独自承受。更让我感动的是她自己也十分努力,于2013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作为一个女子实属不易。有了以上的所思所想,这些人、这些事,乃是我一生为之骄傲的幸运与财富。我深知这些感激之言微不足道,但我还是要祝愿所有的师长、朋友和家人幸福安康。
王永健 谨识
丙申六月十五于三厚堂书斋